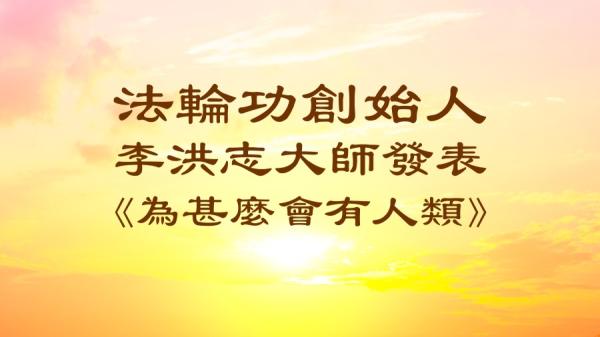故国神游•两宋风华 (54) —— 神宗求变推诚至 安石经国择术先(上)
宋神宗登基时,大宋已经开国百年。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大宋朝一直遵循着祖宗之成法,谨慎守护着祖宗之基业。但是宋神宗登基之后,他不甘做一个守成之君。对内,他希望一革时弊;对外,他志在开疆扩边。而大宋也因为神宗时代的到来,开启了一场前途未卜的百年未有之变局。

王安石的画像(公有领域)
上次我们说到宋神宗。在他登基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一直在向朝中大臣们访求至道,探讨变革之路。他求治求变的重点,主要是在理财、富国、备边、强兵这些问题上。但是,当时的元老重臣们多数都是从仁宗朝时期过来的。在仁宗朝时,曾经发生过两件大事,一件是宋夏战争,另一件是庆历新政。这两件大事,对这些元老重臣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
先说宋夏战争。当时宋夏交兵,朝臣们有主战的,有主和的,有冒进的,有妥协的。但是经过了二十几年时间的沉淀之后,他们就越发地趋同一致:对于边事问题有点谈兵色变。
当然这个不能简单地就归结于说他们软弱、懦弱。比较客观的讲,他们应该是有了更多角度的综合考量。所以,在边事方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和态度。并且他们也提出了对宋神宗的期许,希望这位官家“二十年为可言用兵”。
再说另一件事:庆历新政。这些元老重臣们当时也都是亲历者。当年他们就看到,有时候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制度,真的到了执行阶段,到了实操层面的时候,才会发现有种种之前考虑不到的,或者是即使考虑到了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。所以经历过这些之后,老臣们在政治方略上就越发地趋近于保守和谨慎。那这就与宋神宗的锐意有为、积极进取大为不同。
所以,宋神宗虽然是踌躇满志,但是当他放眼朝堂的时候,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,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。
宋神宗登基时,王安石并不在朝中。他还在仁宗朝的时候,因为母亲去世,就居丧守孝去了。之后,又贯穿英宗一朝,都没有再回到朝廷。但是王安石本人虽然不在朝中,却是声名远播。原因就是他在仁宗朝时屡次辞官。
我们知道,宋朝的士大夫是以名节相上,所以王安石辞官的举动,就使他成为了淡泊名利、志向高洁的现实典范。在王安石的《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:“馆阁之命屡下,安石屡辞;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,恨不识其面,朝廷每欲畀以美官,惟患其不就也。”
提起“馆阁之职”,我们之前讲宋太宗的部分讲到过它,乃是清切之要职,是美差。那对于这样的美差,王安石却是“屡辞”,就是多次拒绝。所以,“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,恨不识其面”。这种美差,别人都是求之不得,而王安石却是避之不及。
所以,大家就觉得王安石特别超凡脱俗,还说要没见过王安石本人,简直都是人生之遗憾,引以为恨。所以,王安石的名气就越来越大,以至于“朝廷每欲畀以美官,为患其不就也”。意思就是,朝廷每次要想给王安石升个职,或者是任命个好差事,唯恐他不接受,就到了这种程度。
还有一段记载也非常生动。王安石在仁宗朝时,曾经做过“修起居注”,就是负责记录皇帝的活动言论的官职。当时,朝廷让他接受这个任命的时候,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
史书中的原文是这样讲的:“明年,同修起居注,辞之累日。阁门吏赍敕就付之,拒不受;吏随而拜之,则避于厕;吏置敕于案而去,又追还之;上章至八九,乃受。”
意思就是他收到任命之后,一连几天表示不接受。所以,阁门吏“赍敕就付之”。阁门吏,就是朝廷派来传话的人,相当于办事员。阁门吏就拿着敕书,就是任命王安石修起居注的诏书,上门来催促他接受任命。
王安石还是不接受,这个办事员就冲着王安石行礼,反正是礼毕事成。王安石于是就赶紧躲了起来,办事员追赶在后,一个躲一个追。最后王安石灵机一动,躲到厕所里去了。办事员一看也不能对着厕所行礼,干脆把敕书往桌面上一放就走人了,他就算交差了。王安石的反应也非常快,他从厕所里狂奔而出,追上办事员,硬是把敕书塞还给了他。
事后,王安石又连续上章八、九次,表示辞谢不接受。当然,这次朝廷也是下定了决心,就是不批准王安石的辞谢,磨了好久,最后,王安石才同意去修起居注。所以,听完这个故事,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,为什么之前说“朝廷每欲畀以美官,为患其不就也”。因为要想给王安石加个官,升个职,实在太累了。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