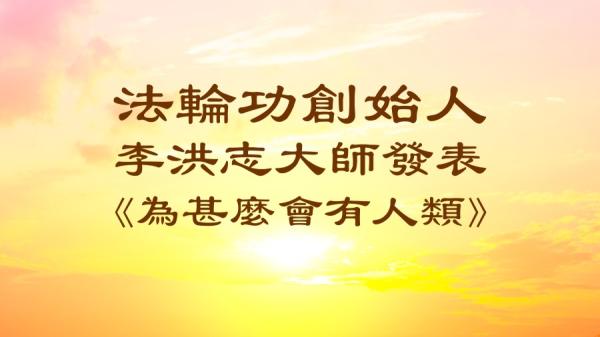汉朝第一贤妃班婕舒
班婕妤(公元前48年~公元2年),出生于楼烦(今山西朔城区)的功勋门第。她父亲班况在汉武帝时驰骋疆场,立下抗击匈奴的汗马功劳。班婕妤自幼聪明伶俐,容颜秀丽,文采出众,擅长诗赋,史称她“善诗赋,厚美德”。汉成帝建始元年(公元前32年),班婕妤被选入宫,初为最低级别的“少使”。她博通文史,在一众后妃中脱颖而出,成为汉成帝的宠妃,她的身份也从“少使”一跃成为“婕妤”。

班婕妤(公有领域)
以贤淑辅助君王
西汉第十二位皇帝汉成帝仪表堂堂,自幼研习儒家经典。汉成帝曾有胆略与志向,即位后拔擢在汉元帝时期一直以来被抑制的儒生群体。《汉书》记载,成帝令史学家刘向集合大批儒生“校经传之诸子诗赋”,对西汉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
汉成帝的身边最初有两大才女:许皇后和班婕妤。班婕妤是汉成帝最中意的妃子。她常开导成帝,劝其勤政。她熟知史事,那些古老的典故在她口中经常娓娓道来,为汉成帝开导内心的积郁;她擅长音律,丝竹之声细腻柔润,从她的指尖流淌。她既是温柔可人的侍妾,更像是汉成帝精神境界的良师益友。班婕妤盛宠十多年,曾经生有一个皇子,却早早夭折,但这不幸并没有影响她给自己的定位:以贤淑辅助君王。因为她熟读史书,她总是鼓励汉成帝励精图治。她也的确因其才情和贤德深受汉成帝宠爱。许皇后慢慢失宠,但班婕妤不忍排挤许皇后,还尽量回避汉成帝对自己的专宠。论贤德,论才情,班婕妤在后宫中有口皆碑。
汉成帝一度想和班婕妤形影不离,特别命人制作了一辆豪华的辇车,要和班婕妤同车出游,不想遭到班婕妤正色拒绝。她说,古代圣贤之君,都有名臣在侧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末主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,才有嬖幸的妃子在坐,最后落到国亡毁身的境地。臣妾如果和皇帝同车出进,那不就跟她们一样了?汉成帝认为她言之成理,只好打消了同辇出游的念头。晋朝顾恺之在他所画的《女史箴图》中,描绘了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乘一驾肩舆的情景,图中人物宛然,细节体物精微,所画妇女尤端庄娴静。图画意在劝导嫔妃们慎言善行,普天下女子也可以此为鉴。
班婕妤婉谢了汉成帝的溺宠,却赢得了西汉实际掌权者皇太后王政君的夸赞,说:“古有樊姬,今有班婕妤。”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夫人,当楚庄王沉迷于打猎时,樊姬以自身不食禽兽之肉来劝谏他,最终使楚庄王改过自新,勤于政事。樊姬的劝谏和辅助使得楚庄王成为一代明君。班婕妤的德行堪与樊姬媲美,以班婕妤的气度和助力,汉成帝果真能勤力朝政,贤明治国该多好啊。然而,历史的轨迹并不完全以人力而为,福祸相依、负阴抱阳,一代贤妃的道路上又会出现什么枝叉呢?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。

班婕妤以美好的德行流传千古 (台北故宫博物院)
激流勇退宠辱止于心
鸿嘉三年(公元前18年),汉成帝微服巡行,在阳阿公主府邂逅了赵飞燕。赵飞燕轻盈的身姿、倾国倾城的容貌,深深迷住汉成帝。赵飞燕姐妹随即入宫,夜夜笙歌,贵倾后宫。班婕妤逐渐失宠。赵飞燕对成帝谗言佞语,说皇后在宫中设坛祈禳诅咒宫廷,成帝大怒,将皇后废黜昭台宫中,又把皇后妹妹许谒问斩。赵氏姐妹进一步蛊惑成帝问责班婕妤。
面对污蔑,班婕妤从容奏道:“妾闻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修正尚未得福,为邪欲以何望?若使鬼神有知,岂肯听信谗说?万一无知,咒诅何益,妾非但不敢为,也是不屑为!”在复杂的宫廷漩涡中,一个女子的修养和见地在生死关头发挥了作用,班婕妤表达的意思很清晰:“人的福寿是命中注定的,非人力所能改变。做好事尚且不一定得福,做坏事又想求什么呢?苍天若有知,岂肯听信小人出于私欲的诅咒话呢?这样的事我不屑去做。”
想那汉成帝也不是胸无点墨,只不过为情色所迷,身不由己。他为班婕妤的坦诚感动,又念及昔日恩情,便赐黄金百斤,命班婕妤退处后宫,免予置罪。接着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,又封赵合德为昭仪,居昭阳宫。该宫全用黄金、白玉、明珠、翠羽装饰,奢华无比。面对这样已经浑噩又不求上进的君主,班婕妤失望至极。她不屑于后宫争风吃醋的生活,请辞去长信宫服侍太后。
唐●李益《宫怨》诗曰:“露湿晴花宫殿香,月明歌吹在昭阳。似将海水添宫漏,共滴长门一夜长。”描述她为:此后每当黎明即起,厚重的长信宫门打开,一个瘦削的身影便出现在台阶之上,冰冷的晨风吹来远处昭阳宫里帝妃们杯羹残酒的喧笑声,而打扫台阶的班婕妤只有落叶为伴,每日默默品味着痛彻心扉的滋味。
情深至淡中正平和
在这种心境下,那首史上著名的《怨歌行》应运而生。“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,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,凉飙夺炎热。弃捐箧笥中,恩情中道绝。”它又题为《团扇诗》,班婕妤做此赋以自伤悼,她思念深爱的成帝,甚至看到飞鸟掠过,都想像它身上带有昭阳殿的日影。她在诗中自比秋扇。洁白的细绢剪裁的团扇,天热时与主人形影相随,到了凉秋时节,则被弃置箱中。后世便以“秋凉团扇”作为女子失宠的象征,又称“班女扇”。在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后,班婕妤将全部情感融入一把小小的扇子之中。这首诗从头至尾无一字凄凄惨惨的啼哭,但字字贴切,表层咏扇,深层自伤。
为什么一首怨妇诗成为千古名篇?汉代文学以辞赋华丽夸张为盛,班婕妤的这首诗却恰好相反,它平淡朴实,内容和措辞上都达到了一种“情深至淡”的境界。
汉成帝也爱好文学,他虽迷恋赵飞燕的妩媚,或许也曾为“团扇诗”暗自赞叹不已。从汉成帝给赵飞燕的一封信可露端倪。汉成帝信中问赵飞燕:夫人,你为什么表里不一,为什么不能做到“推诚写实”呢?这是否意味着成帝还是喜爱班婕妤的诗赋而没有明说呢?“推诚写实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,但它背后的感情曲折,颇耐人寻味。
《礼记●中庸》曰: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后人评论班婕妤的诗赋:哀而不伤、怒而不怨,深得儒家之风。当十载恩爱化缥缈,她的满腹幽怨却以温润之笔娓娓道出,符合儒家的“中正平和”,也体现出她内心深处具备道家的平淡自持。
汉成帝不久便死在赵合德的“温柔乡”。班婕妤到成帝陵守墓以终其生,伴着冢形碑影,陪伴抛弃她的帝王,五年后离开了人世,后葬于延陵。从班婕妤最后的结局来看,虽然她失去了帝王的宠爱,但得以安静度过余生,并在地下永眠在成帝身边。班婕妤的退出宫斗的选择不失为一种修养和明智。
虽然班婕妤得宠时的辉煌不过十余年,但她的美德却流传千古。与她对照,赵氏姐妹被冠以“妖妃”的骂名,遗臭万年。在汉成帝薨逝后,她们一个畏罪自尽,一个在后宫因得罪了王太后,获罪而死,无一善终。
班婕妤的后人班固、班昭为她在史书中正了名。特别是班昭从姑祖母班婕妤身上看到女性“柔顺”、“敬慎”的品德,是班氏后代女性学习的典范,从而写下《女诫》教育女儿们。